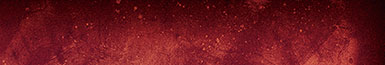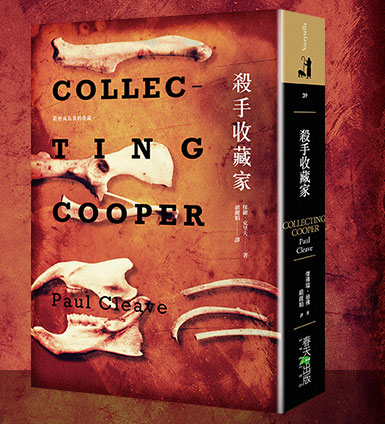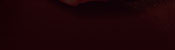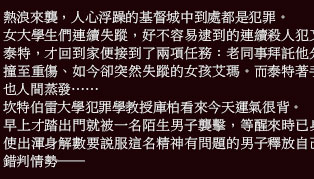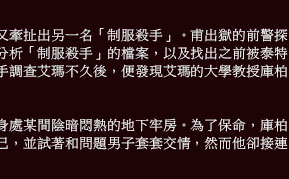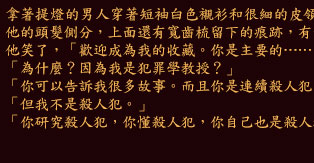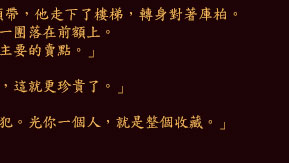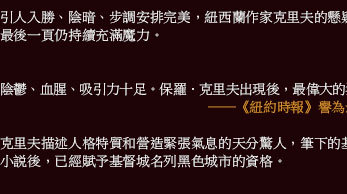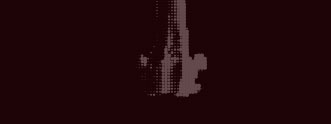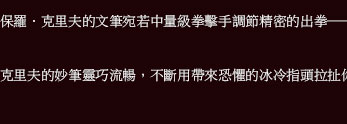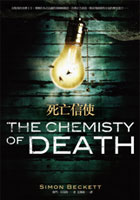楔子
艾瑪.格林希望老人別死了。有時候,在生命中會碰到這樣的時刻,心裡想著這樣,卻期待實際情況是那樣。咖啡店裡倒是一片死寂。過去一小時內才來了兩名顧客,都只點了咖啡,即使今天是星期一,即使生意很清淡,咖啡店老闆才不會讓員工提早下班,而且生意不好,他的脾氣也好不到哪裡去。後面的停車場裡停了她的車、她老闆的車和另外兩輛車。邊上有個大垃圾箱,旁邊疊了幾個牛奶箱,空氣中泛著高麗菜的味道。並沒有什麼遮蔽了光線。有一些啦,但仍亮到能看見老人的身體陷入了前座,嘴巴開開的,眼睛閉著,頭倒向一邊,兩年前爺爺也正是這個模樣,他進了浴室後就沒出來,他們只好破門而入。
她走到車子旁邊朝裡面看。一條口水從他的下唇垂到胸口。他的髮線已經後退到再往後一點點就能算是禿頭了。她認出他是誰了。幾個小時前他來過咖啡店。點了咖啡和司康餅,拿著報紙坐到角落,想解開填字遊戲。「魔鬼住的地方,」他壓低聲音不斷複述這句話,同時用筆敲桌子,她走過去時從他肩膀上瞥了一眼,想到了答案,不過只有兩個空格。可基督城有三個字。「地獄,」她對他說,他微微一笑,道了聲謝,感覺挺和藹。
希望他只是睡著了,她想敲窗戶,又怕萬一他睡著了,會被她嚇一跳驚醒,那就尷尬了。但萬一他不是睡著了呢?或許他的心臟幾秒前才停止跳動,還有機會救回他。不過,感覺也不對,因為他一個多小時前就出了咖啡廳。不太可能死前還在車裡坐了這麼久,除非他把填字遊戲帶到車上玩。好吧,或許魔鬼把他抓走了。她透過車窗看看裡面,把手往車窗伸過去,但沒碰到窗戶。別管了,等下有人看到就讓別人來處理吧。但如果她真的不管,死掉的老人可能要等到早上才有人發現,他還可能變得更窮,車子的音響也被偷走了。
如果是她坐在停著的車子裡,剛嚥下最後一口氣,她會希望經過的人都對她視而不見嗎?
她敲敲窗戶。老人動也不動。她又敲了幾下。沒反應。她心一沉,抓住了門把。門沒鎖。她迅速拉開車門,用幾根手指探探他脖子上的脈搏,手腕切斷了老人下巴上的唾液,像條脫離了網的蜘蛛絲掛在她的手臂上。他的皮膚仍有溫度,但摸不到脈搏,她的手指慢慢移動……
他深吸一口氣,往後縮了一下。「搞什麼?」他劈頭就罵,用力眨著眼睛,好讓視線更清楚。「喂,喂,妳在幹嘛?」他大吼。
「我……」
「不要臉的婊子,小偷,」他的口氣一點也不像她爺爺—至少爺爺在得阿茲海默症前絕不會亂罵人—他抓住她的手,把她拉進車裡。「妳想要……」
「我以為……」
「婊子!」他大吼,然後對她啐了一口。她聞到老人獨有的汗味和食物的味道,他的衣服也有老人味,瘦骨嶙峋的手把她抓得很緊。她很想吐,她的背痛起來了,自從去年出過車禍後,她就常常背痛,她伸手去掰他的手,想脫離他的緊握。
「妳想偷我的東西,」他說。
「不是,才不是,我在……在……」她淚流滿面,說不出口,「你點了咖啡跟……司康餅,我,我以為你……」靠得這麼近,他的氣息燠熱潮濕,她的妝都要花了。她想說的話一直哽在喉嚨裡。
他放開她,摑了她一巴掌。力道很重。活了十七年,她還沒被別人這樣下重手打過。她的頭往旁邊一甩,臉頰火辣辣發熱。然後他的手摸到了她的胸口,一開始她以為他要佔她便宜,接著卻被他用力一推,她只看得到滿天金星和漩渦,背部撞到了地面,還好她的兩隻手撐住了身子。
車門猛然關上。引擎發動了。他搖下窗戶,對她吼了幾句,才把車開走,但引擎聲蓋過了他的吼聲,她滿耳朵血,什麼也聽不到。他往出口疾駛,太貼近牆壁,撞到了垃圾箱,車身刮出了長長的凹痕,她本來以為他會停車,繼續對她亂嚷,可是他沒停下來,急急衝到街上,另一台車傳出了尖銳的煞車聲,有人吼了一聲「王八蛋」。
她坐在地上哭了起來,覺得很生氣,手提包丟在一旁,裡面的東西都落進了柏油路面上的水坑裡。她第一個念頭是進店裡去告訴老闆發生了什麼事,不過他一定會說是她的錯。她老闆有這個問題,什麼都是別人的錯,碰到今天的情況,他會覺得她想要他來負責。她站起身來,看看自己的手掌。右手破皮了,裂開的皮膚很像破掉的氣球。還好沒有流血。
她擦擦眼淚。「王八蛋,」她低聲說。溫暖的風吹過來,拉扯她掌心的破皮,被吹開的皮膚像小小的降落傘。她把東西裝回提包裡,然後又在裡面找鑰匙,但是鑰匙不見了。她蹲回地上。走到停車場的時候,她好像把鑰匙拿在手裡,對不對?她不太確定,想要回頭去找,一轉身就看到鑰匙在一輛骯髒老舊的豐田後輪下。她走過去,彎下腰想撿鑰匙。這時有人朝著她跑過來。她抬頭一看,男人的身影擋住了光線,謝謝老天爺,有人來幫忙了。
「謝……」她只說了一個字,他就跳到她身上,令她滿心驚恐。
她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。她想掙脫,他卻抓住她的頭往地上撞,用力到停車場的燈光都暗了下來。她可以感覺到世界離她而去。她以為她在努力對抗,但她不確定,感覺比較像自己落入了一個夢。祖父對她微笑,車裡的老人,早些她打翻了一杯咖啡,被老闆罵了,男友要跟她過夜,她以為撒旦住在基督城,建立了住所,讓他的朋友在這座城裡肆虐,然後她知道一切都是她的想像,但再怎麼努力,她還是失去了知覺。
等她恢復意識的時候,毫無頭緒到底幾點了。就像去年出車禍的時候一樣。那時她被車撞了,但她什麼也不記得。不記得意外前那個小時,也不記得意外後那一天。這次她記起來了。她躺在床墊上,但翻過身的時候,碰不到床墊的邊緣。她的手腕疼痛難耐,被綁在身後,雙腿也被綁住了,連到把她手腕綁在一起的東西。最糟糕的是頭痛,眼睛後的壓力好強,蓋住眼睛的東西應該也把眼睛壓住了。她又餓又渴,周圍的空氣又悶又熱。應該有三十幾度吧。一片漆黑。她哭了起來。這裡不是醫院。她被綁住了,而且要熱死了。
腳步聲。地板的吱嘎聲。開鎖聲,然後是開門聲。有人走過來。她聽到了呼吸聲。她想講話,可是開不了口。她想到爸媽,想到朋友,還有她的男朋友。她想到咖啡廳裡的老人,對自己承諾,要是能活著離開,她再也不伸手助人了。
「喝。」
男人的聲音。嘴巴上的壓力解除了。她一定可以說點什麼,讓自己脫離這種處境。她可以說動他,把她放走。
「求求你,求求你,」她哭著說,「不要傷害我。我不想受傷,求求你,我求你了,」她滿臉淚水。她從來沒這樣痛哭過。她知道她也從來沒這麼怕過。這人會害她,不論他用什麼手段,她都得承受,承受一輩子,她要發瘋了。按著她的本性,她要死了。
但她可以撐過去。她會活下來。她知道,因為,因為……這原本就不是她的命運。她不可能現在就要死了。不合理。沒道理。她哭得更厲害了。
「求求你,」她說。
塑膠瓶子壓到了她的嘴唇上。
「水,」他把瓶子抬起來,水流入了她的口中。她恨他,但她渴得受不了,只好喝下去。她才喝了幾口,他就把瓶子拿走了。
「等一下再給,」他說。
「你,你是誰?你要對我怎麼樣?」
「不要問了,」他說,她嘴巴上的壓力又回來了,似乎是膠帶。「妳需要留著力氣,」他告訴她。「下禮拜我幫妳計畫了很特別的事情,」他說,「這些都不需要了,」他補了一句,她感覺到刀子滑到了衣服下,然後他把她的衣服割開了。
1
燠熱的空氣裡,操場上的灰塵揮之不去。蒼蠅蚊子都把我的脖子當成機場跑道。高大的水泥牆隔開了外面的聲音,生活的聲音,例如踢足球和玩牌,又例如被人揍扁。右側多了起重機跟鷹架,工人正在擴建已經爆滿的監獄,空氣中布滿了塵土和泥灰,就像早冬的霧氣,厚到什麼都看不清楚,有可能剛跑過一群驚慌亂竄的乳牛,也有可能是一群想要逃獄的犯人。我的衣服有股霉味,感覺很硬;四個月前就折起來塞在紙袋裡,但總比工作睡覺吃飯都穿在身上的那套囚犯連身服好。皮膚上仍留著汗漬跟囚禁的感覺。從柏油路升上來的熱氣包住了我的兩隻腳。握起拳頭,仍能感覺到把我跟人世隔開的金屬和混凝土牆,就像有人被截肢後依然能感覺到不存在的那條腿。過去四個月,我完全與世隔絕。除了外邊的世界,也不跟其他犯人打交道。日復一日,周圍的牢房都是戀童癖跟形形色色的人渣,他們不能回到人群中,不然可能會有人的喉嚨被割開。這四個月有如四年那麼長,但還好沒那麼糟。我的牙齒沒被打掉,也沒有每天晚上被迫雞姦。在混凝土跟鋼鐵構築的世界中,旁邊每個人都痛恨警察,尤甚於彼此痛恨,我又剛好當過警察。身邊這些性侵孩童的禽獸令我作嘔,但換成其他人就更糟糕了。他們大多不跟人來往,整天幻想讓他們被逮捕的那些事情。幻想能回到那樣的生活。
監獄的守衛從入口處看著我。他們似乎很擔心我會闖回監獄。我覺得我很像電影裡的角色;迷失的人,在不同的時間醒來,必須抓住別人的肩膀,問今天是幾月幾號,連幾年都不知道,卻只引來詫異的眼光,覺得你是傻瓜。我當然知道今天的日期。被扔進監獄那天我就在等這天來到。衣服感覺鬆了,因為我變瘦了。監獄食物是營養不良的同義詞。
九點鐘的太陽無情地照下,在我身後留下長長的影子。看向四面八方,地面上似乎都有水,薄薄一層,在熱氣中閃閃爍爍。踩在柏油路上,每走一步都要把鞋底從地上拔起來。我得用手蓋著臉,免得陽光照進眼睛。我才出獄二十五秒,已經不記得入獄前有沒有碰過這麼熱的日子。過去四個月來,我第一次照到這麼強烈的陽光,蒼白的皮膚已經要曬傷了。在背後的高牆裡被困住的時間愈久,這個特別的星期三感覺愈遙遠。入獄後,時間感也被擾亂了。外面有幾部訪客的車子,靠在其中一輛車上的男人看著我。他穿著卡其褲,白襯衫的腋下有一圈黑,自從上次見到他,他也瘦了點,但仍留著平頭,表情也一樣,近來他似乎也只有這種表情。遠處有什麼東西燒起來了,我聞到了煙味。我對著陽光閉上眼睛,讓陽光曬熱我的皮膚,曬到痛了,等我睜開眼睛,施羅德已經離開靠著的車子,快走到我面前了。
「泰特,見到你真好,」施羅德說,他走到我跟前,我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很熱很濕,我好久沒跟別人握手了,但我還記得握手的感覺。監獄的食物還沒把我的腦子蝕光。「怎麼樣?」
「你覺得呢?」我邊問邊放開了他的手。
「嗯,我猜還好吧,」施羅德下了結論。他只是沒話找話說,大家都這樣。兩隻看起來很疲憊的鳥兒從我們身邊低空飛過,尋找更涼爽的地方。「我想,可以讓你搭便車。」
監獄的入口旁停了一台白色的小巴士,下半部蓋滿了塵土,上半部稍微好一點。另外兩個今天出獄的人已經坐在車上,兩人都剃了光頭,雨點圖案的刺青從眼角往外流,他們分坐兩側,眼睛看著窗外,不想跟彼此扯上關係。一個體格很壯的矮個子從監獄裡神氣活現地走出來,右手的指頭都不見了,讓他的拳頭看起來像高爾夫球桿的桿頭,壯碩的手臂向兩側鼓起,包住巨大的胸膛,和更誇大的自尊心。他瞪了我一眼,然後爬上小巴士的後座。我看不出一個星期吧,他們就會回來了。
我們四個都是今天出獄,跟他們在同一部車上共度二十分鐘,一點都不讓我覺得興奮。我也不怎麼想跟施羅德共度這二十分鐘就是了。
「謝謝,」我對他說。
我們朝著他那台深灰色的便衣警車走去,來這裡的路程讓車子沾滿了塵土,輪胎側邊的字母因此更模糊了。我上了車,裡面比外面更熱。我撥弄空調,把通風口朝向自己。後視鏡裡的基督城監獄變得愈來愈小,最後被一大排樹遮住了。我們上了高速公路,向右轉朝著城裡前進。我們經過了很多用鐵絲網圍住的土地,上面的草都乾了。地裡有好幾台牽引機,厚厚的塵土如雲般升起,上面的駕駛從臉上擦掉了清晨的汗水。離開了工地後,空氣就清澈了。
「想過現在要做什麼嗎?」施羅德問。
「為什麼問這個問題?你要給我重操舊業的機會嗎?」
「是呀,應該會有好結果吧。」
「那我去當農夫好了。感覺很愜意。」
「我不認識當農夫的人,泰特,不過我覺得你一定會變成最糟糕那種。」
「是嗎?哪一種?」
他不答腔。他認為要是我當農夫,一定會射殺欺負同類的牛隻。我想像自己一週七天都坐在牽引機上,把牛群從這塊田趕到那塊田,不過,再怎麼努力,腦海中的想像都如過眼雲煙。快到城裡了,車子也變多了。
「聽我說,泰特,我想過了,我現在看事情的方法也有點不一樣了。」
「怎麼不一樣?」
「這座城。社會,我不知道。你怎麼說基督城來著?」
「破敗了,」我回答,是真的。
「是啊。感覺基督城已經分崩離析好一陣子了。但看起來……看起來,我不知道該怎麼說。情況似乎沒有好轉。你三年前離開警隊後,就不清楚情況了,我們人力不足。失蹤人口節節上升。男人,女人,早上出了門,然後就不見了。」
「說不定他們受夠了,自己逃走了,」我提了個可能的原因。
「並不是。」
「你閒聊一定要聊這種話題嗎?」
「難道你想聊過去四個月的經歷嗎?」
我們經過了一塊田,有兩個農夫在燒垃圾,多半是砍下來的樹枝,黑色的濃煙快速衝到空中,像雨雲一樣掛著,沒有微風提供動力。農夫站在牽引機旁,雙手扠腰看著火堆,熱氣讓他們周圍的空氣變得朦朦朧朧。氣味從通風口進入車裡,施羅德關掉了空調,車裡的溫度跟著上升。然後我們穿過了一道兩公尺高的灰色磚牆,上面寫了基督城幾個大字,後面卻未接著歡迎您。事實上,有人用噴漆蓋住了城字,寫上救救我們。各個方向的車子都開得很快,大家都急著要到某個地方。施羅德又開了空調。我們到了離開監獄後第一個大交叉路口,停下來等紅燈,在對面的加油站裡,有台四輪傳動車在倒車時撞上了加油泵,所有的員工圍成一圈觀看,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加油站前的板子告訴我自從我離開後,汽油的價格又上漲了百分之十。我猜氣溫上升了百分之四十,犯罪率上升了百分之五十。基督城有好多統計數字,其中百分之九十跟壞事有關。加油站有一整面牆都畫滿了塗鴉。
綠燈亮了,約莫十秒鐘都沒有車子移動,因為最前面那個人正拿著手機在吵架。我一直覺得車胎要融化了。我們各有所思,然後施羅德打破了沉默。「泰特,重點在於,這座城一直變。我們抓了一個壞人,又有兩個人補上。每況愈下,要失控了。」
「卡爾,已經失控一陣子了。早在我離開警隊前就很糟糕了。」
「嗯,現在似乎愈來愈糟糕。」
「為什麼我覺得有點不對勁?」我問。
「什麼不對勁?」
「你來接我出獄。卡爾,你要什麼就直說吧。」
他用手指敲著方向盤,直勾勾看著前方,視線鎖死在車流上。白光從所有平滑的表面上反射出來,他媽的什麼都快看不到了。我很擔心,還沒到家我的眼球就要融掉了。「在後座,」他說。「有份資料需要你看看。」
「除了戴上太陽眼鏡外,我什麼都不需要。你有備用的嗎?」
「沒有。看看吧。」
「卡爾,不管你打什麼算盤,我都不想答應。」
「我要把另一個殺人犯抓起來。你也不同意嗎?」
「只能說你滿嘴屁話。」
「一年前我認識的泰特就會同意了。他會問我怎麼樣才能幫得上忙。一年前的泰特就算我推辭,也會伸出援手。你還記得嗎?你還記得一年前的自己嗎?還是蹲了四個月,你什麼都不記得了?」
「我當然沒忘。我記得我查到了你不知道的東西,你卻不肯聽。」
「天啊,泰特,你整個扭曲事實了。你妨礙調查,你偷了不屬於你的東西,你騙我,你真的很煩。事實上,你殺了人,你撞了一名少女,害她進了醫院。」
去年,我在追查連續殺人犯,有人死了。壞人。那時候我不知道其中有個壞人,失手殺了他。罪惡感讓我變了一個人,我開始酗酒。酒後出了車禍,車禍又讓我戒酒了。
「你不用教訓我什麼才是事實,」我想到我的女兒,冰冰冷冷在地裡躺了三年,再也不會回來,然後想到住在療養院裡的妻子,只剩一具軀殼,裡面那個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已經不見蹤影。
「你說得對,」他說。「誰比你更明白事實呢?你不需要別人來說教。」
「不論如何,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。」
「為什麼?被關的時候找到了上帝嗎?」
「上帝根本不知道有監獄這個地方,」我告訴他。
「聽我說,泰特,這一仗我們快輸了,我需要你幫忙。一年前那個人,他不在乎越界。該做的他都做了。他不在乎後果。他不在乎法律。我現在不要你表現得跟他一樣。我只要你幫忙。運用你的觀察。去年那個無所畏懼的男人現在連觀察的能力都沒有了嗎?」
「因為那人最後去坐牢了,沒有人關心他,」口中吐出的話比心裡想的更憤慨。
「不,泰特,那人去坐牢,因為他喝醉了,差點撞死人。來吧,我只要你幫忙看看資料就好。看一遍,告訴我你有什麼想法。我不求你去幫我追查嫌犯或親自動手。事實上,我們都看不出什麼,靠太近了—他媽的,你要做什麼,採取什麼行動,都沒關係,那就是你最擅長的。那就是你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。」
「你太誇張了,」我告訴他。
「還想利用你的自大,」他的視線從路上離開了一秒鐘,對我一笑。「但那筆錢很好用,我可沒亂說。」
「錢?怎樣,警隊要付我薪水嗎?我才不相信。」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聽我說,有一筆獎金。三個月前是五萬塊,現在提高到二十萬了。能提供線索讓警方逮捕罪犯,就可以拿到這筆錢。泰特,不然你還有什麼事好做?起碼先看看資料。給你自己一個機會—」
他的手機響了。剛才那句話還沒說完。他拿起手機,只說了幾個字,幾乎都在聽,我不用聽就知道,一定是壞消息。我在當警察的時候,沒有人會打電話來告訴我好消息。沒有人打電話來感謝我抓到了罪犯,買披薩和啤酒請我,說一句幹得好。施羅德放慢了車速,緊緊抓著方向盤。他偏離了車道,避開最近一場意外留下的一大攤安全玻璃,玻璃碎塊跟鑽石一樣,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。我想著獎金,還有可以拿這筆錢來做什麼。我凝望窗外,看著一對穿著黃色反光背心的測量員在量街道,計畫過一陣子要拓寬或收窄道路,或者只是為了消耗基督城的道路施工預算。施羅德打了方向燈,把車開到路邊,有人對我們按了喇叭,還比了中指。施羅德繼續講手機,同時迴轉了車子。我想到一年前的我,但我不想再變成那個人了。施羅德掛了電話。
「泰特,我真的很抱歉,突然有急事。我不能送你回家了。我在城裡讓你下車,好嗎?」
「我能說不要嗎?」
「你有錢坐計程車嗎?」
「你覺得呢?」其實我塞了五十塊錢到褲子口袋裡,就是為了今天可能會用到,但四個月前把衣服脫掉後再穿回來,五十塊已經換到別人的口袋裡了。
我們到了基督城的外圍。車子很多,少了一條車道,好把幾棵跟電線重疊的大樹修剪一下,卡車和設備擋住了路,但工人都坐在樹蔭下,熱到無法開工。我們到了城裡的警察局。他把車開了進去。前面是一台巡邏車,兩名警員正從後座拖出一個男人,他對著他們尖叫,想要咬人,跟得了狂犬病一樣,警察看起來則很想要消滅這隻病犬。施羅德從口袋裡拿出三十塊給我。「應該夠你坐回家了,」他說。
「我走路就好,」我推開了車門。
「別這樣,泰特,拿去吧。」
「別擔心—我不是生你的氣。我被關太久了,想運動一下。」
「這種天氣你還走回家,會熱死你。」
我不要他幫忙。問題是天氣熱到車子的烤漆都要脫落了。門一開熱氣就撲了上來,拂過我的皮膚,吸走所有的水氣。連我的眼睛都好像沾滿了沙子。我拿了錢。「我會還你。」
「把資料拿走,就兩不相欠。」
「不要,」嘴上這麼說,卻感覺得到資料夾的存在,拉著我,充滿吸引力的暴力內容對我低語,告訴我打開了資料夾,就能看到讓我重返那個世界的地圖。「我沒辦法。我的意思是……我就是做不到。」
「拜託,泰特。你還能做什麼?你有妻子要照顧。要繳貸款。你四個月沒有收入。你繳不出錢了。你需要工作。你需要這份工作。我需要你接下這份工作。還會有哪個王八蛋要雇你啊?聽我說,去年你抓到了連續殺人犯,但你覺得會有人在意嗎?不論你再怎麼為自己辯護,再怎麼考量對錯,事實永遠不會改變—你現在有前科了。你逃不了。你的生活再也無法回到從前的樣子。」
「卡爾,謝謝你載我一程。起碼也讓我搭了一半的便車。」
走出警局停車場,到了街上,我才低頭看了看資料,裡面全是死亡案件,等著我去翻閱,從一開始就知道我抗拒不了。